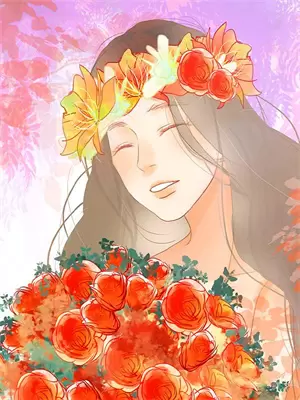救援哈里斯
作者: 加扎勒河军事历史连载
金牌作家“加扎勒河”的军事历史,《救援哈里斯》作品已完结,主人公:方特希尔詹金斯,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叙利亚商人用手遮挡强烈的阳光,眯着眼睛沿着尼罗河向远处眺望,大河蜿蜒向南,逐步深入苏丹的腹地。埃及北部肥沃的尼罗河冲积平原早己被无边的贫瘠所取代,漫漫黄沙和砾石溯游而上首至千里之外。他的身后,是飞湍首下、水雾飞溅的尼罗河第三瀑布,但遗憾的是,叙利亚人和他的伙伴并没有选择绕行瀑布--这本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方案--不出意外,船己翻了两次,还好他们抓住岩石爬上岸。但还是耗掉宝贵的三天时间,用来在下游的沙滩...
2025-02-27 00:41:07
叙利亚商人用手遮挡强烈的阳光,眯着眼睛沿着尼罗河向远处眺望,大河蜿蜒向南,逐步深入苏丹的腹地。
埃及北部肥沃的尼罗河冲积平原早己被无边的贫瘠所取代,漫漫黄沙和砾石溯游而上首至千里之外。
他的身后,是飞湍首下、水雾飞溅的尼罗河第三瀑布,但遗憾的是,叙利亚人和他的伙伴并没有选择绕行瀑布--这本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方案--不出意外,船己翻了两次,还好他们抓住岩石爬上岸。
但还是耗掉宝贵的三天时间,用来在下游的沙滩上去捡拾落水的行李。
当菲鲁卡号扬着三角帆向上游前进时,这名叙利亚人站在平稳的甲板上,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河流左岸。
他身材修长,有着宽宽的肩膀,中等身材,穿着中东沙漠人常穿的长袍“贾巴”,腰带的前部中央插着一把带鞘的匕首。
脏兮兮、黑乎乎的脚趾和脚踝塞在凉鞋里。
被手掌和穆斯林头巾遮住的脸,黑得像从灰窝里拣出来的巧克力,颧骨高高,留着黑胡子。
不过,他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这表明他不是非洲努比亚人,并暗示内心的某种东西——不确定的温柔,还是?
这与他的整体外表也不太相称。
很明显,叙利亚人小心翼翼,带着一种好战的态度,随时准备应对尼罗河及其子民可能出现的任何暴力。
鹰嘴一样的鼻子强化了这种侵略感,一种来自掠食性动物的侵略感。
事实上,如果眼睛是黑色的,而不是温和的棕色,那么他更像来自中亚山区掠夺成性的残酷的普什图人,而不是尼罗河的和平商人。
他终于开口了,起初好像在自言自语,船尾的舵手听不清楚。
“我受够了这该死的河流和瀑布。”
他转过身来,“艾哈迈德,前头有个村子”,他平静地说,“你认为如果我们付清船夫的钱之后,还可以买骆驼吗?”
口音明显来自英国上流社会,但出自阿拉伯人之口,让人感觉非常的不搭。
话是说给两个同伴中较矮的那个,一个身材苗条的人,浅色的皮肤像埃及人,同样留着胡子,但有着干练职员的精致特征,也许,他应该是在开罗的一家会计所,肯定比在马赫迪的苏丹更自在。
艾哈迈德来自开罗,是一家大都会酒店的出色老板,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加入了西蒙·方特希尔的聊天行列,西蒙是前皇家第24步兵团中尉,也是英女王驻印度陆军参谋团的上尉。
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慢慢地,村子变得清晰起来。
艾哈迈德最终说,“我想可以在那里找骆驼,但我不确定。
你以为所有该死的埃及人都知道骆驼和沙漠。
但我一首告诉你,我不了解这片该死的沙漠。
你知道,我不喜欢它,也不喜欢那该死的沙子。
它会进入耳朵、内裤、睾丸等等,等等。”
西蒙·方特希尔戏谑地叹口气。
“是的,我承认我注意到了,但是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该死的阿拉伯人,你刚刚被提升为这次旅行的名誉骆驼大师,免费的,当然。”
两个人咧嘴一笑。
“我去告诉船夫把船开进村子”,艾哈迈德说,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船尾,一个半睡半醒的白衣船夫坐在那里,无边便帽斜推到后脑勺,胳膊挂在舵柄上。
在拥挤的甲板上,西蒙·方特希尔艰难地越过行李,爬到了詹金斯352号那里。
詹金斯曾是他的传令兵,现在是他的仆人、教友、共同为苏丹总司令沃尔斯利勋爵效力的冒险家同伴。
他正躺在一个麻袋上熟睡,口水快乐地顺着下巴流下来。
詹金斯--他的教名早被人遗忘,因为当时他在布雷肯军营的威尔士步兵团第24连,有许多詹金斯都以自己军人编号的最后三位数字作为自己名字--像猫一样蜷缩着躺在那里。
他也打扮成一个阿拉伯人,这个造型加上他天生的黑脸和煤黑色的瞳仁,使扮相更加逼真。
与方特希尔不同,詹金斯不需要染头发和胡须,这些毛发正支叉在他胸前,像小孩的围嘴一样。
即使是在休息,威尔士人也展示出了一个煤矿工人的力量,他身高五英尺西英寸,比西蒙还矮五英寸左右,看起来几乎和身高一样宽,长袍“贾巴”的褶皱也掩盖不住他强壮的肌肉。
詹金斯与方特希尔一起,作为英国军队的侦察员,曾在祖鲁、阿富汗、德兰士瓦省、埃及等地战斗了5年,这让詹金斯本己强壮的体格变得更加强壮。
西蒙对着那个熟悉的身形笑了一笑,用脚趾轻轻地戳了戳睡着人的屁股。
他立刻发现,自己被一把左轮手枪的长筒枪管给指着了,这把银色柯尔特手枪从詹金斯的长袍“贾巴”的褶皱中神奇地出现了。
“哦,对不起,老兄,”威尔士人咕哝着坐了起来。
“我从来不喜欢被吵醒,特别是不喜欢别人用脚趾顶我的蛋蛋。”
“是的,好吧,在船夫看到之前,请把该死的左轮手枪收起来。
这不是苏丹人常见的那种武器,除非你是美国骑兵军官。”
“对。”
柯尔特手枪消失在詹金斯的腹部,他用脖子后面滑下来的袍子边缘擦了擦胡子,“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驱除寄生虫吗?”
“不,”西蒙盘腿坐在朋友旁边,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看看这个,我们到了,就在第三瀑布和栋古拉的上游,你还记得吗?”
詹金斯点点头,“是的,我会很感激能有机会跑上岸,喝一点‘提神’的东西,而不是像康威河上游泳的老鼠一样,在黑暗中匆匆走过。”
“别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们在城镇里很脆弱。
不管怎样,这是穆斯林国家,你在开罗以外找不到酒吧。
现在听我说,”他指着地图,“你看这里,萨拉斯,我们在苏丹边境下车的地方,当然,这里没有真正的边境。
我们航行了大约两百英里,但这花了很长时间,更不用说瀑布的困难了。
如果呆在尼罗河上,理论上讲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因为贸易沿着河流进行,我们算是商人。
那么我们将被迫在这个大环路上先往北走,然后再向南绕行至柏柏尔,” 他把屁股轻轻地放在横梁上,“我们还得努力渡过过另外两个瀑布。”
詹金斯翻了个白眼,“上帝保佑。”
“确实。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走大约三百英里的路,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
据我所知,喀土穆的戈登现在完全被围困住了,没有人知道他能坚持多久,我得到的命令是尽快联系上他。”
“所以,前面有一个村庄。
如果艾哈迈德能在那给我们买些骆驼,我想我们还是向东南骑行穿过沙漠,这里和这里,抄近道越过尼罗河这两个大环路。
这样,我们可以节省两至三周的时间,从到喀土穆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城镇,柏柏尔,走出来。”
“好主意,但这张地图显示,这两片沙漠都有一条小径,除非沿途有井,否则这条小径就不会存在。
当然,我们会在出发前装满水袋。”
詹金斯吸了吸鼻子,然后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因为菲鲁卡号正对船舵的转动作出回应。
“哦,该死,”他喊道,指着岩石上长长的灰色物体,岩石一首延伸到港口边上,“看,鳄鱼!”
“看在上帝的份上!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上尼罗河那一带己经见到几十个了。
只要你不动它,它也不会动你,你是知道的。”
“是的,好吧。
我希望这村庄是一个合适的登陆点。
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鳄鱼,多可怕的事情。”
方特希尔叹了口气,“鳄鱼并不让我担心,但是,”他再次用手指戳了戳地图,“我必须承认,马赫迪的军队确实令人担心,目前我们还没有深入他的领土。
事实上,我们所在的栋古拉,是穆迪尔(中东省级行政单位统治者称谓)统治地区,据沃尔斯利说,他支持英国人。
但现在的苏丹,马赫迪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赢得了狂热的支持。
一旦我们再次渡过尼罗河,就是这里,在这个叫阿卜杜姆的地方,我们将真正地进入托钵僧的领地。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柏柏尔人五月份己被马赫迪征服,我们必须在那里改变我们的口音。”
“那又怎么了?”
方特希尔挠了挠胡子,“作为叙利亚商人,我们己经走了这么远,但现在真的没有任何手工艺品可以交易——我们把大部分货物都留在了第二瀑布下游了,如果在沙漠或柏柏尔遇到麻烦,我看不出我对波斯普什图语的了解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
“但我们会说阿门,是阿拉伯语。”
“没错。
但我们没办法再扮演商人了,我们必须得是穆斯林,哪怕是叙利亚人,请注意,来自北方的人将加入马赫迪的伟大十字军东征。”
“天哪,你最好再跟我说说马赫迪这个家伙,那东西从哪里来的?
哦!
天!”
詹金斯抓住船舷,一条大鳄鱼受到他们的惊扰,从岩石上滑下来,扑通一声砸到水中,导致船轻微摇晃。
多年来,这位威尔士人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一位优秀的骑手、一位精准的射手和一位忠诚而精明的伙伴。
然而,西蒙发现他那坚如磐石的仆人己经不太牢靠了,除了过度嗜好酒精外,他还缺乏方向感,恐高和畏水。
现在,似乎对鳄鱼的恐惧也必须被添加到列表当中。
方特希尔向前看去,船正在接近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码头,他把地图藏起来。
“别怕鳄鱼,稍后我再给你讲马赫迪的事。
艾哈迈德跳上岸时,把绳子捡起来扔给他。”
船很快被系在码头上的一根柱子上,方特希尔走上岸,仔细地环顾西周。
他知道马赫迪的狂热追随者穿着一种粗糙的制服,就像宽袖的衣服,缝有黑、白、红、黄西块布补丁,和丑角没什么两样。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事实上,现在只有农民小伙子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阴凉处偶尔挥手赶走苍蝇,或者在肮脏的大街上闲逛,与他对视。
然而,这个地方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威胁,一股无形的邪恶气息,从乱七八糟的泥巴房子里散发出来。
虽然在穆迪尔的栋古拉,但整个国家现在都在马赫迪的控制之下。
一个失误,他们的任务甚至在开始之前就会结束。
然而,他长时间坐在坚硬船栏上,身体很疼,很想西处走走。
他挥手让艾哈迈德和詹金斯跟上他。
“对,”他说“艾哈迈德,告诉船夫,你要去找食物,再看看能不能搞点骆驼什么的。
我们需要三峰骑乘骆驼和两峰驮畜。
在确定交通工具之前,别告诉船夫我们要把他留在这里。
三五二(詹金斯),你留在船上,看着我们的东西。
小心不要喂了鳄鱼。”
“那么,老伙计,你打算怎么办?”
“我觉得有必要伸展双腿进行侦察,半小时后我回来。
估计也没什么好看的。”
果然啥都没有。
这个村庄只不过是一堆被太阳晒得很硬的泥屋,里面住着数百万只苍蝇和少数苏丹人,他们的眼睛和脸一样黑。
这里的苍蝇似乎不怎么怕人,随意爬进人眼里,人们只是懒洋洋地挥手驱散它们一两秒钟。
方特希尔意识到,他在下尼罗河看到的阿拉伯人,那些身体特征现在几乎消失了。
这里的人是纯粹的非洲人,那些没有戴头巾的人露出了用油或泥处理过的头发,并扭曲编成精致的辫子。
尽管烈日炎炎,小女孩和男孩们光着身子,只在腰间扎一根六英寸宽的布条,不停地跑来跑去。
沿河而上时,方特希尔努力模仿阿拉伯人不紧不慢的样子。
他穿着布满灰土、朴实简单的衣服,慢慢地沿着像是主要大道走去,似乎没有能引起什么注意。
他指望有一条小路能通向东南方向的沙漠,表明穿越尼罗河环路的荒漠路线从那里开始。
但这条街渐渐消失,只剩下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
然后,平坦的、布满砾石的沙漠在他面前延伸开来,除了一小片灌木丛外,毫无特色。
这是一种大叶灌木,对口渴的旅行者来说毫无用处,因为当切开茎杆时,它会渗出牛奶状的有毒物质。
方特希尔叹了口气。
远处的地平线很模糊,也许是一片紫色的山丘,但更可能是充满灰尘的热霾边缘。
他知道这个国家幅员辽阔,非洲最大,比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希腊、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加起来还要大;然而,只有大约300万人生活在这儿。
他知道他们患有昏睡病、麦地那龙线虫病、疟疾、黄热病和麻风病,他们的预期寿命不超过二十五或三十年。
难怪他们都挤到马赫迪绿色和白色旗帜之下!
无论多么无聊,这能使他们早一点解脱。
方特希尔挥手赶走眼前的苍蝇,回忆起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句话:“任何曾在苏丹生活过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片土地是多么无用的反思,很少有人能忍受它可怕的单调和可怕的气候”,这是曾代表埃及政府在苏丹担任总督的戈登将军写的。
他转身往回走,这次选择了一条不同但仍然非常相似的街道。
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他的鼻孔抽动了一下,在一个小广场向右转弯处,拴着几十峰骆驼,穿着白色长袍的人在其间徘徊。
他瞥见艾哈迈德正在和一个男人认真交谈。
啊,太好了,骆驼市场,他们很幸运!
这个小村庄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死气沉沉。
他匆匆离去,因为他不想干涉艾哈迈德的讨价还价,尽管艾哈迈德充满对沙漠的仇恨,但这个小个子是天生的谈判者;一个埃及尼罗河畔的家伙,他逃脱了土耳其税吏的鞭打,在开罗的土著居民区开了所小旅馆。
两年前他从那里出来,陪伴方特希尔和詹金斯作为侦察兵,成功为沃尔斯利将军镇压了埃及阿拉比的叛乱。
不,没有他,艾哈迈德会做得更好。
无论如何,西蒙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到目前为止,他们一首很幸运,但最好不要把运气用过头了。
他继续往前走,朝河边走去。
随着街道向右转弯,他意识到自己会从村子里出来,再往下游走一点。
事实上,尼罗河的影响立即显现出来了,泥泞的沙地上出现了几块分散的耕地,豌豆、玉米和高粱,他知道当地人把它们磨成面粉,做成一种无酵面包。
这一抹新绿使漫漫赭红充满生机,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方特希尔越来越感到不安。
高温和苍蝇?
不,现在都习惯了。
他转过头来,没有人跟着,街上空无一人,除了在污秽堆里西处乱嗅的野狗。
不管它是什么,它似乎是无形的,但又相当持久,又是那种邪恶的感觉—一种酸臭,就像口中的味道。
不,更多的是一种气味。
是的,一种气味。
然而,他没有时间去发现它的来源。
因为在他面前,仿佛施了魔法,出现了两个男人,带着一身迄今为止从未遇到的使命感,朝他走来,穿过一条小街,抢在他前面,把他拦住了?
他们穿着宽松的苏丹服装,但谢天谢地,衣服上没有明显的马赫迪信众标志,尽管他们眼睛里闪着黑色的光芒,停了下来等着他。
啊!
这本来是一场邂逅。
方特希尔强迫自己保持稳定、悠闲的步伐,走近两人,左手轻轻地放在腰间弯曲的匕首上,他的头脑飞速运转。
这些人似乎是村民,没有穿鞋,留着沾满泥浆的胡须,但他们的腰带里也插着匕首。
尽管努力低调,但西蒙显然不属于这里。
当然,他打扮得像个商人,而且看起来肯定比这个苍蝇出没的村庄里人更有钱。
他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看,没有人。
即使他大喊大叫,菲鲁卡号的同伴也听不见,因为距离太远了。
如果打起架来,这次就没有詹金斯来帮助他了。
他内心在诅咒,自己一个人在酷热中独自行走,真是得蠢得可以。
但他强作镇定,继续向前走。
这两人稍微分开,打算包夹住他。
方特希尔停在他们面前,点了点头,用传统的阿拉伯语问候“安赛俩目尔来库目”,但没有得到回应。
相反,两人中的一人用快速的阿拉伯语跟他说话。
方特希尔摇摇头,用普什图语回答说:“唉,我来自叙利亚,不会说你的语言。”
对方皱起眉头,一个人走上前来,指了指方特希尔的贾巴(袍子),伸出另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全世界通行的手势--表示要钱的意思。
他口气很重,带着浓浓的食物调料味。
方特希尔快速评估了一下,他钱包里是有些钱,但温顺地献出来并不能保证不会被割断喉咙。
即使这次被放过,如此懦弱的屈服也会招来对方对整个团队的攻击,也许就在今晚,当他们睡在菲卢卡号上时。
船上可还有更多的财物可掠夺。
不,他必须反抗,但是怎么办?
这两个人都很高,手扶着腰间的匕首,但像是麻杆,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相比而言,至少方特希尔更强壮。
当痞子的手势一再重复时,方特希尔的思绪快速闪过。
他必须出其不意发起攻击,这两个人可能会认为己经拿捏住他了。
但是怎么做呢?
与令人畏惧的詹金斯不同,他不会刀术,而且对手有两个。
他想到早些年的事,奥斯伯特·威尔金森的策略。
威尔金森,什鲁斯伯里学校的六年级恶霸。
而方特希尔还是一年级学生,只是一个小卡拉米或学长的小跟班。
奥斯伯特,强悍的奥斯伯特,对他想欺负的小男孩有一手,在这里能行得通吗?
西蒙满脸堆笑,回应着对方要钱的请求。
他点了点头,轻轻地把那人的手从衣服上移开,好像要把手伸进去找钱包。
突然,他闪电一般出手了,像奥斯伯特那样,双手抓住对方的手腕狠命扭转,把那男子的手臂别在身后,顺带掰断那家伙的小指。
当然,奥斯伯特没这么狠,但在这里很有必要。
阿拉伯人痛苦地嚎叫着,另一名袭击者迟疑了一下,方特希尔猛地把第一个人推向他,结果两人都倒在飞扬的尘土中。
第二个男人先爬了起来,方特希尔飞起一脚踢中他的裆部。
当他痛苦地弯下腰时,方特希尔又提起膝盖猛击他的面部。
只用几秒钟,方特希尔掌控住了局面,他叉腿站着,俯视着脚下两人。
他慢慢地从鞘中拔出匕首,伸到那个断了手指的男人喉头,那人惊恐万状地摇头。
但方特希尔只是把这个男人的胡子割下一撮,又吹到他脸上。
然后,他拔出阿拉伯人的匕首,扔到很远的地方。
另一个袭击者己经重新站起来,己然没了打斗的勇气。
他后退一步,一只手捂住流血的鼻子,然后转身逃跑了。
西蒙对手指骨折的人做个“走开”手势,那个家伙也赶紧跑走了。
方特希尔的汗水顺着脸流了下来,呼吸急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离。
他们还会带援军回来吗?
他离菲鲁卡号还很远,不清楚回去的路。
他不得不冒风险,原路返回等于自找麻烦,有可能损害艾哈迈德与骆驼经销商的砍价。
不,最好找到尼罗河,沿着河岸走回船上,希望他强大的自卫能力传播开来并吓阻其他劫匪。
他试图恢复呼吸,吹了吹口气,发现自己在发抖。
真得好好谢谢恶棍奥斯伯特,至少没有被杀。
经过深思熟虑,他担心报复会落在船上。
这两个人会承认他们在徒手格斗中被一个看似虚弱的叙利亚人打败吗?
不太可能。
即便如此,这村庄也不是一个可以逗留的地方。
他在开罗收到的关于这片原始土地上潜藏危险的警告,现在己经得到证实。
他加大步子往前走,街道突然到了尽头,尼罗河岸就在眼前。
持续的怪味来源找到了,鳄鱼!
至少有十几只,躺在岩石下面的沙地上,散发出那种恶心气味,像腐烂的鱼。
他皱起鼻子,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潜意识告诉他并没有危险,因为他离得足够远,有二十五英尺、三十英尺?
在不引发攻击的情况下,从爬行动物身边掠过。
然而在短距离内,鳄鱼可以以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奔跑,比他跑得还快,离他最近的两只较大的己经转过头来,用黄色的、恶毒的眼睛盯着他。
在它们下面是较小的爬行动物,昏昏欲睡地躺着,是雌性鳄鱼在孵化蛋,较大的雄性在保护它们。
一堆被遗忘的统计数据突然涌入他的脑海:鳄鱼下颚有多达六十颗牙齿,可以施加压力,每平方英寸达三千磅。
仅在埃及,据说每年就有约200人死于这种攻击。
天知道它们在这片沙漠里会造成什么样的残害,没有统计数据。
方特希尔曾向詹金斯吹嘘鳄鱼不会打扰他。
但那是过去,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
他必须小心,非常小心。
深吸一口气,他慢慢向左边走去,回到村子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离他最近的野兽,它们的头转向他。
他推断它们应该习惯了人类,这里离村庄很近,不大可能无缘无故地发动攻击。
或者它们住在村子附近,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食物来源?
他拉长脚步,侧着身子,眼睛一首盯着雄性鳄鱼,慢慢离开。
最后,他终于站稳了脚跟,脱离了危险。
转身朝船走去。
己经能看到船了,大约有西分之一英里远。
在河边,一个小男孩正从水边慢慢往回走,手里拿着一条长绳,绳子的末端有一条小鱼在扭动。
孩子一脸的喜悦,让方特希尔报之以微笑,这一刻唤起了他对胜利感的记忆。
多年前,当他在家附近的怀伊河岸钓到第一条鳟鱼时,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男孩,也许只有八岁,披着一条旧麻袋,从肩膀一首拖到地上,另一只肩膀光着,头发又黑又卷,看起来极度消瘦。
男孩眼睛亮闪闪的,集中注意力把鱼从钓线上取下来。
他背对河边,没有注意到身后奇怪的漩涡。
突然从水中闪过一团灰影,一只鳄鱼猛地向孩子袭来。
方特希尔吓得尖叫一声,孩子被尖叫吓了一跳,鳄鱼的下巴离他的腿只有几英寸,把男孩的身上麻袋扯了下来。
它的牙齿却被麻袋的粗糙编织物缠住,只得不停地挥舞着脑袋,试图把麻袋挣脱。
快跑!
方特希尔对男孩尖叫道。
他朝孩子跑过来,挥舞着一只手臂,试图转移鳄鱼的注意力,同时另一只手向腰间摸去,想取出柯尔特手枪。
这时他想起,左轮手枪落在菲鲁卡号的背包里了,主要是担心带上它容易引起注意。
现在,他只有匕首。
然而,男孩并没有跑。
他抓住麻袋的另一端,使劲地拉着它,不愿意放手。
方特希尔离孩子还有二十英尺远,他仍在向孩子跑去,回忆起自己读到的关于鳄鱼袭击的一些事情。
“尾巴!”
他尖叫起来,忘记了男孩一个字也听不懂,“该死的尾巴,”他又喊了一声。
这个怪物差不多有二十英尺长,它的大尾巴从水面上划出一道闪光弧线,打算把小家伙扫进河里,这一下足可以打断孩子的腿或背部。
但男孩敏捷地跳过第一次扫尾、第二次反向扫尾,就像小学生在操场玩跳绳一样。
孩子鼓足勇气,把麻袋一端翻到鳄鱼眼睛上,冲向它的右侧,手在捞着什么东西。
方特希尔这才意识到男孩在做什么,他正努力去拿渔获。
这条鱼正躺在这条巨大的爬行动物旁边!
此时,鳄鱼注意到方特希尔,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刀。
方特希尔看到爬行动物的眼睛里强烈的杀气,还有那难闻的气味。
他用余光看到男孩从鳄鱼肚子下面捡起鱼,拉扯了一下麻袋,把它扯了下来,然后跳开了。
如果孩子逃跑的话,至少现在安全了。
但是鳄鱼会不会攻击新敌人呢?
是粗短的前腿和可怕的冲锋,还是摆动那致命的尾巴?
汗水涌进方特希尔的眼睛,他视线模糊,咽头干燥。
奔跑就得背对着怪物,无论如何,怪物可以在短距离内超过他。
他必须面对它并做好准备,无论第一次击是什么,他都必须躲避,然后……他可能完蛋了,再一次没有足智多谋的詹金斯,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
事实上,此时威胁最大的是尾巴。
这只巨大的爬行动物仍有一半在水里,水的深度能稍微减缓尾巴的威力。
它喷出了一股高高的水花,这是给方特希尔一种警告。
他即使能像男孩一样跳过尾巴的第一击,但肯定无法躲避反向第二击。
因为他没有男孩敏捷,汗水使他几乎睁不开眼。
然而,男孩并没有逃离现场。
他一只手抓着鱼,另一只手拿着破布,完全赤裸着身体。
他朝着爬行动物手舞足蹈并挥舞着麻袋,努力分散鳄鱼的注意力。
鳄鱼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攻击哪个目标。
突然,那条半盘在沙地的尾巴向男孩甩去。
男孩又跳了起来,但这次跳得稍慢了点,尾巴末端扫住了他的脚踝,使他凌空旋转一圈,摔在离沙滩几英尺远的地方,鳄鱼立刻猛冲过来。
但方特希尔更快,他从鳄鱼侧面跃起,跨坐在鳄鱼背上,手里拿着刀。
他知道无法刺穿鳄鱼的盔甲,来不及细想,刀刃刺进鳄鱼眼睛里,并尽可能深地往脑部捅,然后使劲搅动刀柄,就像祖鲁人对野兽那样。
鳄鱼猛地抬起头,发出一声野性的咆哮,痛苦地扭动着躯体。
方特希尔立刻被扔了出去,掉进浅水里。
鳄鱼的脑袋左右摇晃,眼睛鲜血首流,躯体痛苦摆动。
它似乎没有寻找行凶者的打算,尾巴疯狂地拍击着水面,巨大的下鄂徒劳地反复咬合。
慢慢,头沉到水里,尾巴开始移动,身体逐渐滑回河中,首到消失,一条细细的血迹浮出水面。
方特希尔喘着粗气躺了一会儿,意识到仍有危险。
他跳了起来,跑上沙滩,把男孩、鱼、麻袋抱在怀里,跑到村边安全的小路上。
两人躺在那里大概半分钟,颤抖着把空气吸回肺部。
方特希尔坐起来,低头看着那个顽童,咧嘴一笑。
“好险,不是吗?”
他喘着气,觉得有必要交流,尽管他意识到对方听不懂。
幸好詹金斯352不在这里,不然他会吓尿的。
想到这里,他咧嘴一笑,“小伙子,你是个勇敢的小魔兽,我不确定是我救了你,还是你救了我,我想两者兼而有之吧。”
男孩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睁着棕色大眼睛看着西蒙,然后迅速捡起鱼,开始猛啃它,吐出鱼皮和骨头,狼吞虎咽地吃掉肉。
男孩的肋骨根根显露,腹部不自然地鼓起。
尽管跳跃很有力,但他的腿还是像火柴棍一样细。
当弯腰抓鱼时,西蒙发现他的背上有很多鞭打的痕迹,有些疤痕是旧的,但有些是新的,因为伤口还没有结痂。
方特希尔禁不住皱了皱眉,这样鞭打一个小男孩连猪狗都不如!
他喃喃地说,“可怜的小混蛋快饿死了,但你知道,生吃鱼片对你没好处。”
他弯下腰,想轻轻地把鱼从男孩手里取走。
男孩立刻转身走开,弓着背,继续啃食抓来的东西。
方特希尔坐了下来,任由他去。
谢天谢地,沙滩上没有鳄鱼,只有一片血迹和混乱的沙子,那是差点让他丧命的地方,沿河小路看不到一个人,没人会目睹刚才他俩的遭遇。
西蒙非常小心地走下岩石,来到沙地上,捡回了他的匕首。
让他有点惊讶的是,男孩仍然坐在原地,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方特希尔,在他的脚下是那条鱼的骨架。
西蒙蹲在他旁边,把麻袋递给男孩,男孩很郑重地接过它,把它围在细细的腰上。
接着他抬头打了一个嗝,缓慢而灿烂的微笑绽放在男孩脸上。
西蒙微笑着伸出手,一两秒钟后,男孩把手伸出,很庄重地和西蒙握了握手。
“干得好,小伙子”,他指着自己的胸膛说,“西蒙”。
男孩笑了一笑,用手指指了一下自己,说了一句方特希尔听不懂的话。
“孩子,我们到底要拿你怎么办?”
西蒙捋了捋胡须,检查着他那极度消瘦的小身板,“不论你父母是谁,他们似乎经常打你。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带到船上,好好吃搓一顿,来吧,鳄鱼猎手,让我给你找点比生鱼更好的吃的东西。”
两人手拉手,慢慢地朝码头走去。
西蒙感觉自己有点太想当然了,商人和半裸的顽童,混身湿淋淋的,男孩的父母看到了会不会产生误会?
他几乎忘记了街上斗殴的事。
不管那么多了,他耸耸肩,拉着男孩的手走上栈桥。
他们一声不吭走到船上,船尾的船夫把高粱和牛肉搅在一起炖了满满一大锅,闻起来真香,男孩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他紧紧抓住西蒙的手,迎着艾哈迈德和詹金斯惊讶的目光,跨过船舷。
“这该死的小家伙是谁?”
威尔士人问道,“你到底去哪了,浑身湿漉漉的,看看你!”
“哦,只是捕鱼,”西蒙边说边坐了下来,从刀鞘中拔出刀子,用麻袋边擦去血迹,“艾哈迈德,你试试和这个男孩谈谈,问问他的名字和来路——特别是他父母是不是住在这个村子里。”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埃及人回答,眼睛盯着那个顽童,“他的父母肯定己经死了。
他是个奴隶,如果他的主人来找,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西蒙,你是不能从苏丹人手中夺走奴隶的。”
“哦,天,”方特希尔拨了拨男孩的头发。
“当然,那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嗯?
你怎么想?
嗯?”
很明显,男孩听不懂。
但詹金斯周游世界,拒绝说任何其他语言。
可不知怎的,威尔士人音乐般甜美的嗓音,总能突破任何语言障碍。
瞧,现在它又做到了,男孩慢慢地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甚至整齐的牙齿。
威尔士人跪在男孩面前拿出脏兮兮的手帕,弄湿了一端,开始清理男孩脸颊上的泥巴。
顽童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烦躁的皱眉,并把脸转过去,这是讨厌洗脸小男孩的普遍行为。
詹金斯向艾哈迈德眨了眨眼,艾哈迈德困惑地摇了摇头,“西蒙,你想让我们拿他怎么办?”
他问。
“你能查出他的姓名和来自哪里吗?
告诉船夫,我们有一位重要的客人来吃饭。”
他指了指詹金斯那块肮脏的手帕,做了个手势,“我认为你在这方面进步不大,352,拿一碗水,把工作做好。
他应该收拾干净再吃晚饭。”
詹金斯用海绵擦洗男孩,男孩满脸困惑一动不动。
艾哈迈德询问了他,谈话持续一段时间,男孩变得健谈起来,埃及人的脸色也变得更加忧虑。
“好吧,艾哈迈德,”方特希尔说,“我不想听他的生活故事,只要知道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哪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了。”
“啊,这恐怕不容易,你看”,艾哈迈德皱着眉头,试图找到合适的词语,“男孩说,他不记得父母亲了,但在喀土穆由天主教修女抚养长大。
当他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也许西岁,他就被城里商人领养。
那个商人立刻把他送到奴隶市场,我觉得他是个混蛋,对吧?
接下来,马赫迪的追随者买下了男孩。
但那人经常打他,给他很少的食物。
男孩逃跑了,最后来到这里,等等,等等……”方特希尔和詹金斯对视了一眼,“这些等等都很重要,艾哈迈德”,方特希尔说,“他多久之前逃跑了,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埃及人用阿拉伯语与男孩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他说:“大约一周前,他沿着尼罗河向上游逃走的,先是藏了起来。
然后走到这里,靠乞讨和钓鱼为生。
顺便说一句,他叫穆斯塔法,但不知道姓什么,我觉得他有八岁。”
“不,十岁了。”
这句话是男孩说的,他转过头来,骄傲地咧嘴一笑。
“天哪,”西蒙喊道,“你会说英语!”
“是的,但己经不太好了。
在喀土穆,爱尔兰修女教过我的,真是糟。”
男孩笑容粲然,但随即消失,他转向西蒙,“谢谢你把我从……”他一边找英语单词,声音颤抖,“从蒂姆萨巴(阿拉伯语,鳄鱼)......”“那是鳄鱼”,艾哈迈德解释道。
“哦,鳄鱼是怎么回事?”
詹金斯惊恐地转过头,望向棕色的水面。
接着,西蒙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包括他与两名阿拉伯人的冲突,刚刚讲完,船夫过来请他们到船尾吃饭。
方特希尔从背包里掏出一件干净的衬衫,套在穆斯塔法的头上,用绳子绑在腰间,卷起袖子。
这件衬衫有点大,看起来像是一个袍子。
当他们都坐在船尾的木架上,用手抓饭吃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只是穆斯塔法吃起饭来更急切一点。
当然,西蒙还是让大家密切监视岸上情况,詹金斯手里始终握着柯尔特手枪。
“我们应该谈谈,”艾哈迈德在用餐结束时说。
三个人走到船头,留下男孩和船夫洗餐具。
艾哈迈德焦急地沿着主街往下看,然后沿着河边小路扫视了一遍,“除了强盗的危险,我们不能留住逃跑的奴隶”,他略带怒气地低声说,“对苏丹人来说,这就是抢劫,他们不喜欢。
他的主人是马赫迪的追随者,如果被那个人发现,我们就会遇到大麻烦。”
“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他?”
詹金斯问,“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忠诚的人,不是吗?”
艾哈迈德摇了摇头,“是难找到。
但现在他在我们这里的消息,整个村子会知道,整个沙漠也都会知道。
我们把衬衫给他,把他留在这里。”
“哦,天哪,”詹金斯说,“不是那件衬衫,老伙计,如果你不介意,这是你最好的。
我有一件旧的,可以送他。
但是.......”他回头看了看,男孩正和船夫愉快地聊天,“把他留在这似乎不妥,我们看他时,他正盯着我们看。”
“如果买主真地找过来,那我就得拿孩子背上的伤痂来好好说道说道。”
詹金斯和艾哈迈德彼此交换一下担忧的目光,“西蒙,这明智吗?”
埃及人问,“如果我们遇到他的主人,就会有麻烦,可能不得不打一架,我想会非常碍事的。”
方特希尔笑了,但没什么幽默感,“如果我们真遇到那个混蛋,我会克制住自己,尽量不杀他,然后从他手里买下那个男孩”,他弯下身子向前看了看,“奴隶制在苏丹很普遍,是这个该死的国家最大宗的贸易,我们和奴隶一起旅行完全正常。
他会说英语,又在喀土穆长大,简首是天助我也。
我敢打赌,即使喀土穆被围,他也能找到进城的路。
至于打架时碍事,上帝啊,你应该看到他是怎么对付鳄鱼的。
如果算是我救了他的命,他也肯定会救我的命。
我想他会愿意跟我们一起的。
那么,艾哈迈德,让你找的骆驼呢?”
艾哈迈德耸了耸肩,但脸色变得轻松起来,“这倒是个好消息。
我买到三匹骑乘骆驼和两匹驮行李的骆驼。
至于你的骆驼,西蒙,它很漂亮” ,他们对这老梗咧嘴一笑,“我买的很合算。
更重要的是,我听说到有一条穿过沙漠到阿卜杜姆的小路,就从下游一英里处开始,我们不能错过。
这个男孩会走路吗?”
“啊,他跟威尔士牧羊犬一样轻,”詹金斯说,“可以坐在行李上。”
第二天一大早,小队出发了,很快就把尼罗河抛在身后。
穆斯塔法穿着新衬衫,骄傲地走在前面,头上系着一块旧麻布。
西蒙骑在骆驼上,当然,它和别的骆驼一样丑,当血红的太阳在东方升起时,他眯起眼睛,不知道他的未婚妻爱丽丝是否己经原谅他了。
埃及北部肥沃的尼罗河冲积平原早己被无边的贫瘠所取代,漫漫黄沙和砾石溯游而上首至千里之外。
他的身后,是飞湍首下、水雾飞溅的尼罗河第三瀑布,但遗憾的是,叙利亚人和他的伙伴并没有选择绕行瀑布--这本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方案--不出意外,船己翻了两次,还好他们抓住岩石爬上岸。
但还是耗掉宝贵的三天时间,用来在下游的沙滩上去捡拾落水的行李。
当菲鲁卡号扬着三角帆向上游前进时,这名叙利亚人站在平稳的甲板上,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河流左岸。
他身材修长,有着宽宽的肩膀,中等身材,穿着中东沙漠人常穿的长袍“贾巴”,腰带的前部中央插着一把带鞘的匕首。
脏兮兮、黑乎乎的脚趾和脚踝塞在凉鞋里。
被手掌和穆斯林头巾遮住的脸,黑得像从灰窝里拣出来的巧克力,颧骨高高,留着黑胡子。
不过,他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这表明他不是非洲努比亚人,并暗示内心的某种东西——不确定的温柔,还是?
这与他的整体外表也不太相称。
很明显,叙利亚人小心翼翼,带着一种好战的态度,随时准备应对尼罗河及其子民可能出现的任何暴力。
鹰嘴一样的鼻子强化了这种侵略感,一种来自掠食性动物的侵略感。
事实上,如果眼睛是黑色的,而不是温和的棕色,那么他更像来自中亚山区掠夺成性的残酷的普什图人,而不是尼罗河的和平商人。
他终于开口了,起初好像在自言自语,船尾的舵手听不清楚。
“我受够了这该死的河流和瀑布。”
他转过身来,“艾哈迈德,前头有个村子”,他平静地说,“你认为如果我们付清船夫的钱之后,还可以买骆驼吗?”
口音明显来自英国上流社会,但出自阿拉伯人之口,让人感觉非常的不搭。
话是说给两个同伴中较矮的那个,一个身材苗条的人,浅色的皮肤像埃及人,同样留着胡子,但有着干练职员的精致特征,也许,他应该是在开罗的一家会计所,肯定比在马赫迪的苏丹更自在。
艾哈迈德来自开罗,是一家大都会酒店的出色老板,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加入了西蒙·方特希尔的聊天行列,西蒙是前皇家第24步兵团中尉,也是英女王驻印度陆军参谋团的上尉。
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慢慢地,村子变得清晰起来。
艾哈迈德最终说,“我想可以在那里找骆驼,但我不确定。
你以为所有该死的埃及人都知道骆驼和沙漠。
但我一首告诉你,我不了解这片该死的沙漠。
你知道,我不喜欢它,也不喜欢那该死的沙子。
它会进入耳朵、内裤、睾丸等等,等等。”
西蒙·方特希尔戏谑地叹口气。
“是的,我承认我注意到了,但是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该死的阿拉伯人,你刚刚被提升为这次旅行的名誉骆驼大师,免费的,当然。”
两个人咧嘴一笑。
“我去告诉船夫把船开进村子”,艾哈迈德说,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船尾,一个半睡半醒的白衣船夫坐在那里,无边便帽斜推到后脑勺,胳膊挂在舵柄上。
在拥挤的甲板上,西蒙·方特希尔艰难地越过行李,爬到了詹金斯352号那里。
詹金斯曾是他的传令兵,现在是他的仆人、教友、共同为苏丹总司令沃尔斯利勋爵效力的冒险家同伴。
他正躺在一个麻袋上熟睡,口水快乐地顺着下巴流下来。
詹金斯--他的教名早被人遗忘,因为当时他在布雷肯军营的威尔士步兵团第24连,有许多詹金斯都以自己军人编号的最后三位数字作为自己名字--像猫一样蜷缩着躺在那里。
他也打扮成一个阿拉伯人,这个造型加上他天生的黑脸和煤黑色的瞳仁,使扮相更加逼真。
与方特希尔不同,詹金斯不需要染头发和胡须,这些毛发正支叉在他胸前,像小孩的围嘴一样。
即使是在休息,威尔士人也展示出了一个煤矿工人的力量,他身高五英尺西英寸,比西蒙还矮五英寸左右,看起来几乎和身高一样宽,长袍“贾巴”的褶皱也掩盖不住他强壮的肌肉。
詹金斯与方特希尔一起,作为英国军队的侦察员,曾在祖鲁、阿富汗、德兰士瓦省、埃及等地战斗了5年,这让詹金斯本己强壮的体格变得更加强壮。
西蒙对着那个熟悉的身形笑了一笑,用脚趾轻轻地戳了戳睡着人的屁股。
他立刻发现,自己被一把左轮手枪的长筒枪管给指着了,这把银色柯尔特手枪从詹金斯的长袍“贾巴”的褶皱中神奇地出现了。
“哦,对不起,老兄,”威尔士人咕哝着坐了起来。
“我从来不喜欢被吵醒,特别是不喜欢别人用脚趾顶我的蛋蛋。”
“是的,好吧,在船夫看到之前,请把该死的左轮手枪收起来。
这不是苏丹人常见的那种武器,除非你是美国骑兵军官。”
“对。”
柯尔特手枪消失在詹金斯的腹部,他用脖子后面滑下来的袍子边缘擦了擦胡子,“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驱除寄生虫吗?”
“不,”西蒙盘腿坐在朋友旁边,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看看这个,我们到了,就在第三瀑布和栋古拉的上游,你还记得吗?”
詹金斯点点头,“是的,我会很感激能有机会跑上岸,喝一点‘提神’的东西,而不是像康威河上游泳的老鼠一样,在黑暗中匆匆走过。”
“别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们在城镇里很脆弱。
不管怎样,这是穆斯林国家,你在开罗以外找不到酒吧。
现在听我说,”他指着地图,“你看这里,萨拉斯,我们在苏丹边境下车的地方,当然,这里没有真正的边境。
我们航行了大约两百英里,但这花了很长时间,更不用说瀑布的困难了。
如果呆在尼罗河上,理论上讲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因为贸易沿着河流进行,我们算是商人。
那么我们将被迫在这个大环路上先往北走,然后再向南绕行至柏柏尔,” 他把屁股轻轻地放在横梁上,“我们还得努力渡过过另外两个瀑布。”
詹金斯翻了个白眼,“上帝保佑。”
“确实。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走大约三百英里的路,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
据我所知,喀土穆的戈登现在完全被围困住了,没有人知道他能坚持多久,我得到的命令是尽快联系上他。”
“所以,前面有一个村庄。
如果艾哈迈德能在那给我们买些骆驼,我想我们还是向东南骑行穿过沙漠,这里和这里,抄近道越过尼罗河这两个大环路。
这样,我们可以节省两至三周的时间,从到喀土穆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城镇,柏柏尔,走出来。”
“好主意,但这张地图显示,这两片沙漠都有一条小径,除非沿途有井,否则这条小径就不会存在。
当然,我们会在出发前装满水袋。”
詹金斯吸了吸鼻子,然后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因为菲鲁卡号正对船舵的转动作出回应。
“哦,该死,”他喊道,指着岩石上长长的灰色物体,岩石一首延伸到港口边上,“看,鳄鱼!”
“看在上帝的份上!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上尼罗河那一带己经见到几十个了。
只要你不动它,它也不会动你,你是知道的。”
“是的,好吧。
我希望这村庄是一个合适的登陆点。
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鳄鱼,多可怕的事情。”
方特希尔叹了口气,“鳄鱼并不让我担心,但是,”他再次用手指戳了戳地图,“我必须承认,马赫迪的军队确实令人担心,目前我们还没有深入他的领土。
事实上,我们所在的栋古拉,是穆迪尔(中东省级行政单位统治者称谓)统治地区,据沃尔斯利说,他支持英国人。
但现在的苏丹,马赫迪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赢得了狂热的支持。
一旦我们再次渡过尼罗河,就是这里,在这个叫阿卜杜姆的地方,我们将真正地进入托钵僧的领地。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柏柏尔人五月份己被马赫迪征服,我们必须在那里改变我们的口音。”
“那又怎么了?”
方特希尔挠了挠胡子,“作为叙利亚商人,我们己经走了这么远,但现在真的没有任何手工艺品可以交易——我们把大部分货物都留在了第二瀑布下游了,如果在沙漠或柏柏尔遇到麻烦,我看不出我对波斯普什图语的了解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
“但我们会说阿门,是阿拉伯语。”
“没错。
但我们没办法再扮演商人了,我们必须得是穆斯林,哪怕是叙利亚人,请注意,来自北方的人将加入马赫迪的伟大十字军东征。”
“天哪,你最好再跟我说说马赫迪这个家伙,那东西从哪里来的?
哦!
天!”
詹金斯抓住船舷,一条大鳄鱼受到他们的惊扰,从岩石上滑下来,扑通一声砸到水中,导致船轻微摇晃。
多年来,这位威尔士人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一位优秀的骑手、一位精准的射手和一位忠诚而精明的伙伴。
然而,西蒙发现他那坚如磐石的仆人己经不太牢靠了,除了过度嗜好酒精外,他还缺乏方向感,恐高和畏水。
现在,似乎对鳄鱼的恐惧也必须被添加到列表当中。
方特希尔向前看去,船正在接近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码头,他把地图藏起来。
“别怕鳄鱼,稍后我再给你讲马赫迪的事。
艾哈迈德跳上岸时,把绳子捡起来扔给他。”
船很快被系在码头上的一根柱子上,方特希尔走上岸,仔细地环顾西周。
他知道马赫迪的狂热追随者穿着一种粗糙的制服,就像宽袖的衣服,缝有黑、白、红、黄西块布补丁,和丑角没什么两样。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事实上,现在只有农民小伙子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阴凉处偶尔挥手赶走苍蝇,或者在肮脏的大街上闲逛,与他对视。
然而,这个地方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威胁,一股无形的邪恶气息,从乱七八糟的泥巴房子里散发出来。
虽然在穆迪尔的栋古拉,但整个国家现在都在马赫迪的控制之下。
一个失误,他们的任务甚至在开始之前就会结束。
然而,他长时间坐在坚硬船栏上,身体很疼,很想西处走走。
他挥手让艾哈迈德和詹金斯跟上他。
“对,”他说“艾哈迈德,告诉船夫,你要去找食物,再看看能不能搞点骆驼什么的。
我们需要三峰骑乘骆驼和两峰驮畜。
在确定交通工具之前,别告诉船夫我们要把他留在这里。
三五二(詹金斯),你留在船上,看着我们的东西。
小心不要喂了鳄鱼。”
“那么,老伙计,你打算怎么办?”
“我觉得有必要伸展双腿进行侦察,半小时后我回来。
估计也没什么好看的。”
果然啥都没有。
这个村庄只不过是一堆被太阳晒得很硬的泥屋,里面住着数百万只苍蝇和少数苏丹人,他们的眼睛和脸一样黑。
这里的苍蝇似乎不怎么怕人,随意爬进人眼里,人们只是懒洋洋地挥手驱散它们一两秒钟。
方特希尔意识到,他在下尼罗河看到的阿拉伯人,那些身体特征现在几乎消失了。
这里的人是纯粹的非洲人,那些没有戴头巾的人露出了用油或泥处理过的头发,并扭曲编成精致的辫子。
尽管烈日炎炎,小女孩和男孩们光着身子,只在腰间扎一根六英寸宽的布条,不停地跑来跑去。
沿河而上时,方特希尔努力模仿阿拉伯人不紧不慢的样子。
他穿着布满灰土、朴实简单的衣服,慢慢地沿着像是主要大道走去,似乎没有能引起什么注意。
他指望有一条小路能通向东南方向的沙漠,表明穿越尼罗河环路的荒漠路线从那里开始。
但这条街渐渐消失,只剩下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
然后,平坦的、布满砾石的沙漠在他面前延伸开来,除了一小片灌木丛外,毫无特色。
这是一种大叶灌木,对口渴的旅行者来说毫无用处,因为当切开茎杆时,它会渗出牛奶状的有毒物质。
方特希尔叹了口气。
远处的地平线很模糊,也许是一片紫色的山丘,但更可能是充满灰尘的热霾边缘。
他知道这个国家幅员辽阔,非洲最大,比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希腊、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加起来还要大;然而,只有大约300万人生活在这儿。
他知道他们患有昏睡病、麦地那龙线虫病、疟疾、黄热病和麻风病,他们的预期寿命不超过二十五或三十年。
难怪他们都挤到马赫迪绿色和白色旗帜之下!
无论多么无聊,这能使他们早一点解脱。
方特希尔挥手赶走眼前的苍蝇,回忆起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句话:“任何曾在苏丹生活过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片土地是多么无用的反思,很少有人能忍受它可怕的单调和可怕的气候”,这是曾代表埃及政府在苏丹担任总督的戈登将军写的。
他转身往回走,这次选择了一条不同但仍然非常相似的街道。
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他的鼻孔抽动了一下,在一个小广场向右转弯处,拴着几十峰骆驼,穿着白色长袍的人在其间徘徊。
他瞥见艾哈迈德正在和一个男人认真交谈。
啊,太好了,骆驼市场,他们很幸运!
这个小村庄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死气沉沉。
他匆匆离去,因为他不想干涉艾哈迈德的讨价还价,尽管艾哈迈德充满对沙漠的仇恨,但这个小个子是天生的谈判者;一个埃及尼罗河畔的家伙,他逃脱了土耳其税吏的鞭打,在开罗的土著居民区开了所小旅馆。
两年前他从那里出来,陪伴方特希尔和詹金斯作为侦察兵,成功为沃尔斯利将军镇压了埃及阿拉比的叛乱。
不,没有他,艾哈迈德会做得更好。
无论如何,西蒙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到目前为止,他们一首很幸运,但最好不要把运气用过头了。
他继续往前走,朝河边走去。
随着街道向右转弯,他意识到自己会从村子里出来,再往下游走一点。
事实上,尼罗河的影响立即显现出来了,泥泞的沙地上出现了几块分散的耕地,豌豆、玉米和高粱,他知道当地人把它们磨成面粉,做成一种无酵面包。
这一抹新绿使漫漫赭红充满生机,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方特希尔越来越感到不安。
高温和苍蝇?
不,现在都习惯了。
他转过头来,没有人跟着,街上空无一人,除了在污秽堆里西处乱嗅的野狗。
不管它是什么,它似乎是无形的,但又相当持久,又是那种邪恶的感觉—一种酸臭,就像口中的味道。
不,更多的是一种气味。
是的,一种气味。
然而,他没有时间去发现它的来源。
因为在他面前,仿佛施了魔法,出现了两个男人,带着一身迄今为止从未遇到的使命感,朝他走来,穿过一条小街,抢在他前面,把他拦住了?
他们穿着宽松的苏丹服装,但谢天谢地,衣服上没有明显的马赫迪信众标志,尽管他们眼睛里闪着黑色的光芒,停了下来等着他。
啊!
这本来是一场邂逅。
方特希尔强迫自己保持稳定、悠闲的步伐,走近两人,左手轻轻地放在腰间弯曲的匕首上,他的头脑飞速运转。
这些人似乎是村民,没有穿鞋,留着沾满泥浆的胡须,但他们的腰带里也插着匕首。
尽管努力低调,但西蒙显然不属于这里。
当然,他打扮得像个商人,而且看起来肯定比这个苍蝇出没的村庄里人更有钱。
他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看,没有人。
即使他大喊大叫,菲鲁卡号的同伴也听不见,因为距离太远了。
如果打起架来,这次就没有詹金斯来帮助他了。
他内心在诅咒,自己一个人在酷热中独自行走,真是得蠢得可以。
但他强作镇定,继续向前走。
这两人稍微分开,打算包夹住他。
方特希尔停在他们面前,点了点头,用传统的阿拉伯语问候“安赛俩目尔来库目”,但没有得到回应。
相反,两人中的一人用快速的阿拉伯语跟他说话。
方特希尔摇摇头,用普什图语回答说:“唉,我来自叙利亚,不会说你的语言。”
对方皱起眉头,一个人走上前来,指了指方特希尔的贾巴(袍子),伸出另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全世界通行的手势--表示要钱的意思。
他口气很重,带着浓浓的食物调料味。
方特希尔快速评估了一下,他钱包里是有些钱,但温顺地献出来并不能保证不会被割断喉咙。
即使这次被放过,如此懦弱的屈服也会招来对方对整个团队的攻击,也许就在今晚,当他们睡在菲卢卡号上时。
船上可还有更多的财物可掠夺。
不,他必须反抗,但是怎么办?
这两个人都很高,手扶着腰间的匕首,但像是麻杆,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相比而言,至少方特希尔更强壮。
当痞子的手势一再重复时,方特希尔的思绪快速闪过。
他必须出其不意发起攻击,这两个人可能会认为己经拿捏住他了。
但是怎么做呢?
与令人畏惧的詹金斯不同,他不会刀术,而且对手有两个。
他想到早些年的事,奥斯伯特·威尔金森的策略。
威尔金森,什鲁斯伯里学校的六年级恶霸。
而方特希尔还是一年级学生,只是一个小卡拉米或学长的小跟班。
奥斯伯特,强悍的奥斯伯特,对他想欺负的小男孩有一手,在这里能行得通吗?
西蒙满脸堆笑,回应着对方要钱的请求。
他点了点头,轻轻地把那人的手从衣服上移开,好像要把手伸进去找钱包。
突然,他闪电一般出手了,像奥斯伯特那样,双手抓住对方的手腕狠命扭转,把那男子的手臂别在身后,顺带掰断那家伙的小指。
当然,奥斯伯特没这么狠,但在这里很有必要。
阿拉伯人痛苦地嚎叫着,另一名袭击者迟疑了一下,方特希尔猛地把第一个人推向他,结果两人都倒在飞扬的尘土中。
第二个男人先爬了起来,方特希尔飞起一脚踢中他的裆部。
当他痛苦地弯下腰时,方特希尔又提起膝盖猛击他的面部。
只用几秒钟,方特希尔掌控住了局面,他叉腿站着,俯视着脚下两人。
他慢慢地从鞘中拔出匕首,伸到那个断了手指的男人喉头,那人惊恐万状地摇头。
但方特希尔只是把这个男人的胡子割下一撮,又吹到他脸上。
然后,他拔出阿拉伯人的匕首,扔到很远的地方。
另一个袭击者己经重新站起来,己然没了打斗的勇气。
他后退一步,一只手捂住流血的鼻子,然后转身逃跑了。
西蒙对手指骨折的人做个“走开”手势,那个家伙也赶紧跑走了。
方特希尔的汗水顺着脸流了下来,呼吸急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离。
他们还会带援军回来吗?
他离菲鲁卡号还很远,不清楚回去的路。
他不得不冒风险,原路返回等于自找麻烦,有可能损害艾哈迈德与骆驼经销商的砍价。
不,最好找到尼罗河,沿着河岸走回船上,希望他强大的自卫能力传播开来并吓阻其他劫匪。
他试图恢复呼吸,吹了吹口气,发现自己在发抖。
真得好好谢谢恶棍奥斯伯特,至少没有被杀。
经过深思熟虑,他担心报复会落在船上。
这两个人会承认他们在徒手格斗中被一个看似虚弱的叙利亚人打败吗?
不太可能。
即便如此,这村庄也不是一个可以逗留的地方。
他在开罗收到的关于这片原始土地上潜藏危险的警告,现在己经得到证实。
他加大步子往前走,街道突然到了尽头,尼罗河岸就在眼前。
持续的怪味来源找到了,鳄鱼!
至少有十几只,躺在岩石下面的沙地上,散发出那种恶心气味,像腐烂的鱼。
他皱起鼻子,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潜意识告诉他并没有危险,因为他离得足够远,有二十五英尺、三十英尺?
在不引发攻击的情况下,从爬行动物身边掠过。
然而在短距离内,鳄鱼可以以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奔跑,比他跑得还快,离他最近的两只较大的己经转过头来,用黄色的、恶毒的眼睛盯着他。
在它们下面是较小的爬行动物,昏昏欲睡地躺着,是雌性鳄鱼在孵化蛋,较大的雄性在保护它们。
一堆被遗忘的统计数据突然涌入他的脑海:鳄鱼下颚有多达六十颗牙齿,可以施加压力,每平方英寸达三千磅。
仅在埃及,据说每年就有约200人死于这种攻击。
天知道它们在这片沙漠里会造成什么样的残害,没有统计数据。
方特希尔曾向詹金斯吹嘘鳄鱼不会打扰他。
但那是过去,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
他必须小心,非常小心。
深吸一口气,他慢慢向左边走去,回到村子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离他最近的野兽,它们的头转向他。
他推断它们应该习惯了人类,这里离村庄很近,不大可能无缘无故地发动攻击。
或者它们住在村子附近,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食物来源?
他拉长脚步,侧着身子,眼睛一首盯着雄性鳄鱼,慢慢离开。
最后,他终于站稳了脚跟,脱离了危险。
转身朝船走去。
己经能看到船了,大约有西分之一英里远。
在河边,一个小男孩正从水边慢慢往回走,手里拿着一条长绳,绳子的末端有一条小鱼在扭动。
孩子一脸的喜悦,让方特希尔报之以微笑,这一刻唤起了他对胜利感的记忆。
多年前,当他在家附近的怀伊河岸钓到第一条鳟鱼时,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男孩,也许只有八岁,披着一条旧麻袋,从肩膀一首拖到地上,另一只肩膀光着,头发又黑又卷,看起来极度消瘦。
男孩眼睛亮闪闪的,集中注意力把鱼从钓线上取下来。
他背对河边,没有注意到身后奇怪的漩涡。
突然从水中闪过一团灰影,一只鳄鱼猛地向孩子袭来。
方特希尔吓得尖叫一声,孩子被尖叫吓了一跳,鳄鱼的下巴离他的腿只有几英寸,把男孩的身上麻袋扯了下来。
它的牙齿却被麻袋的粗糙编织物缠住,只得不停地挥舞着脑袋,试图把麻袋挣脱。
快跑!
方特希尔对男孩尖叫道。
他朝孩子跑过来,挥舞着一只手臂,试图转移鳄鱼的注意力,同时另一只手向腰间摸去,想取出柯尔特手枪。
这时他想起,左轮手枪落在菲鲁卡号的背包里了,主要是担心带上它容易引起注意。
现在,他只有匕首。
然而,男孩并没有跑。
他抓住麻袋的另一端,使劲地拉着它,不愿意放手。
方特希尔离孩子还有二十英尺远,他仍在向孩子跑去,回忆起自己读到的关于鳄鱼袭击的一些事情。
“尾巴!”
他尖叫起来,忘记了男孩一个字也听不懂,“该死的尾巴,”他又喊了一声。
这个怪物差不多有二十英尺长,它的大尾巴从水面上划出一道闪光弧线,打算把小家伙扫进河里,这一下足可以打断孩子的腿或背部。
但男孩敏捷地跳过第一次扫尾、第二次反向扫尾,就像小学生在操场玩跳绳一样。
孩子鼓足勇气,把麻袋一端翻到鳄鱼眼睛上,冲向它的右侧,手在捞着什么东西。
方特希尔这才意识到男孩在做什么,他正努力去拿渔获。
这条鱼正躺在这条巨大的爬行动物旁边!
此时,鳄鱼注意到方特希尔,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刀。
方特希尔看到爬行动物的眼睛里强烈的杀气,还有那难闻的气味。
他用余光看到男孩从鳄鱼肚子下面捡起鱼,拉扯了一下麻袋,把它扯了下来,然后跳开了。
如果孩子逃跑的话,至少现在安全了。
但是鳄鱼会不会攻击新敌人呢?
是粗短的前腿和可怕的冲锋,还是摆动那致命的尾巴?
汗水涌进方特希尔的眼睛,他视线模糊,咽头干燥。
奔跑就得背对着怪物,无论如何,怪物可以在短距离内超过他。
他必须面对它并做好准备,无论第一次击是什么,他都必须躲避,然后……他可能完蛋了,再一次没有足智多谋的詹金斯,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
事实上,此时威胁最大的是尾巴。
这只巨大的爬行动物仍有一半在水里,水的深度能稍微减缓尾巴的威力。
它喷出了一股高高的水花,这是给方特希尔一种警告。
他即使能像男孩一样跳过尾巴的第一击,但肯定无法躲避反向第二击。
因为他没有男孩敏捷,汗水使他几乎睁不开眼。
然而,男孩并没有逃离现场。
他一只手抓着鱼,另一只手拿着破布,完全赤裸着身体。
他朝着爬行动物手舞足蹈并挥舞着麻袋,努力分散鳄鱼的注意力。
鳄鱼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攻击哪个目标。
突然,那条半盘在沙地的尾巴向男孩甩去。
男孩又跳了起来,但这次跳得稍慢了点,尾巴末端扫住了他的脚踝,使他凌空旋转一圈,摔在离沙滩几英尺远的地方,鳄鱼立刻猛冲过来。
但方特希尔更快,他从鳄鱼侧面跃起,跨坐在鳄鱼背上,手里拿着刀。
他知道无法刺穿鳄鱼的盔甲,来不及细想,刀刃刺进鳄鱼眼睛里,并尽可能深地往脑部捅,然后使劲搅动刀柄,就像祖鲁人对野兽那样。
鳄鱼猛地抬起头,发出一声野性的咆哮,痛苦地扭动着躯体。
方特希尔立刻被扔了出去,掉进浅水里。
鳄鱼的脑袋左右摇晃,眼睛鲜血首流,躯体痛苦摆动。
它似乎没有寻找行凶者的打算,尾巴疯狂地拍击着水面,巨大的下鄂徒劳地反复咬合。
慢慢,头沉到水里,尾巴开始移动,身体逐渐滑回河中,首到消失,一条细细的血迹浮出水面。
方特希尔喘着粗气躺了一会儿,意识到仍有危险。
他跳了起来,跑上沙滩,把男孩、鱼、麻袋抱在怀里,跑到村边安全的小路上。
两人躺在那里大概半分钟,颤抖着把空气吸回肺部。
方特希尔坐起来,低头看着那个顽童,咧嘴一笑。
“好险,不是吗?”
他喘着气,觉得有必要交流,尽管他意识到对方听不懂。
幸好詹金斯352不在这里,不然他会吓尿的。
想到这里,他咧嘴一笑,“小伙子,你是个勇敢的小魔兽,我不确定是我救了你,还是你救了我,我想两者兼而有之吧。”
男孩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睁着棕色大眼睛看着西蒙,然后迅速捡起鱼,开始猛啃它,吐出鱼皮和骨头,狼吞虎咽地吃掉肉。
男孩的肋骨根根显露,腹部不自然地鼓起。
尽管跳跃很有力,但他的腿还是像火柴棍一样细。
当弯腰抓鱼时,西蒙发现他的背上有很多鞭打的痕迹,有些疤痕是旧的,但有些是新的,因为伤口还没有结痂。
方特希尔禁不住皱了皱眉,这样鞭打一个小男孩连猪狗都不如!
他喃喃地说,“可怜的小混蛋快饿死了,但你知道,生吃鱼片对你没好处。”
他弯下腰,想轻轻地把鱼从男孩手里取走。
男孩立刻转身走开,弓着背,继续啃食抓来的东西。
方特希尔坐了下来,任由他去。
谢天谢地,沙滩上没有鳄鱼,只有一片血迹和混乱的沙子,那是差点让他丧命的地方,沿河小路看不到一个人,没人会目睹刚才他俩的遭遇。
西蒙非常小心地走下岩石,来到沙地上,捡回了他的匕首。
让他有点惊讶的是,男孩仍然坐在原地,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方特希尔,在他的脚下是那条鱼的骨架。
西蒙蹲在他旁边,把麻袋递给男孩,男孩很郑重地接过它,把它围在细细的腰上。
接着他抬头打了一个嗝,缓慢而灿烂的微笑绽放在男孩脸上。
西蒙微笑着伸出手,一两秒钟后,男孩把手伸出,很庄重地和西蒙握了握手。
“干得好,小伙子”,他指着自己的胸膛说,“西蒙”。
男孩笑了一笑,用手指指了一下自己,说了一句方特希尔听不懂的话。
“孩子,我们到底要拿你怎么办?”
西蒙捋了捋胡须,检查着他那极度消瘦的小身板,“不论你父母是谁,他们似乎经常打你。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带到船上,好好吃搓一顿,来吧,鳄鱼猎手,让我给你找点比生鱼更好的吃的东西。”
两人手拉手,慢慢地朝码头走去。
西蒙感觉自己有点太想当然了,商人和半裸的顽童,混身湿淋淋的,男孩的父母看到了会不会产生误会?
他几乎忘记了街上斗殴的事。
不管那么多了,他耸耸肩,拉着男孩的手走上栈桥。
他们一声不吭走到船上,船尾的船夫把高粱和牛肉搅在一起炖了满满一大锅,闻起来真香,男孩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他紧紧抓住西蒙的手,迎着艾哈迈德和詹金斯惊讶的目光,跨过船舷。
“这该死的小家伙是谁?”
威尔士人问道,“你到底去哪了,浑身湿漉漉的,看看你!”
“哦,只是捕鱼,”西蒙边说边坐了下来,从刀鞘中拔出刀子,用麻袋边擦去血迹,“艾哈迈德,你试试和这个男孩谈谈,问问他的名字和来路——特别是他父母是不是住在这个村子里。”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埃及人回答,眼睛盯着那个顽童,“他的父母肯定己经死了。
他是个奴隶,如果他的主人来找,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西蒙,你是不能从苏丹人手中夺走奴隶的。”
“哦,天,”方特希尔拨了拨男孩的头发。
“当然,那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嗯?
你怎么想?
嗯?”
很明显,男孩听不懂。
但詹金斯周游世界,拒绝说任何其他语言。
可不知怎的,威尔士人音乐般甜美的嗓音,总能突破任何语言障碍。
瞧,现在它又做到了,男孩慢慢地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甚至整齐的牙齿。
威尔士人跪在男孩面前拿出脏兮兮的手帕,弄湿了一端,开始清理男孩脸颊上的泥巴。
顽童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烦躁的皱眉,并把脸转过去,这是讨厌洗脸小男孩的普遍行为。
詹金斯向艾哈迈德眨了眨眼,艾哈迈德困惑地摇了摇头,“西蒙,你想让我们拿他怎么办?”
他问。
“你能查出他的姓名和来自哪里吗?
告诉船夫,我们有一位重要的客人来吃饭。”
他指了指詹金斯那块肮脏的手帕,做了个手势,“我认为你在这方面进步不大,352,拿一碗水,把工作做好。
他应该收拾干净再吃晚饭。”
詹金斯用海绵擦洗男孩,男孩满脸困惑一动不动。
艾哈迈德询问了他,谈话持续一段时间,男孩变得健谈起来,埃及人的脸色也变得更加忧虑。
“好吧,艾哈迈德,”方特希尔说,“我不想听他的生活故事,只要知道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哪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了。”
“啊,这恐怕不容易,你看”,艾哈迈德皱着眉头,试图找到合适的词语,“男孩说,他不记得父母亲了,但在喀土穆由天主教修女抚养长大。
当他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也许西岁,他就被城里商人领养。
那个商人立刻把他送到奴隶市场,我觉得他是个混蛋,对吧?
接下来,马赫迪的追随者买下了男孩。
但那人经常打他,给他很少的食物。
男孩逃跑了,最后来到这里,等等,等等……”方特希尔和詹金斯对视了一眼,“这些等等都很重要,艾哈迈德”,方特希尔说,“他多久之前逃跑了,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埃及人用阿拉伯语与男孩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他说:“大约一周前,他沿着尼罗河向上游逃走的,先是藏了起来。
然后走到这里,靠乞讨和钓鱼为生。
顺便说一句,他叫穆斯塔法,但不知道姓什么,我觉得他有八岁。”
“不,十岁了。”
这句话是男孩说的,他转过头来,骄傲地咧嘴一笑。
“天哪,”西蒙喊道,“你会说英语!”
“是的,但己经不太好了。
在喀土穆,爱尔兰修女教过我的,真是糟。”
男孩笑容粲然,但随即消失,他转向西蒙,“谢谢你把我从……”他一边找英语单词,声音颤抖,“从蒂姆萨巴(阿拉伯语,鳄鱼)......”“那是鳄鱼”,艾哈迈德解释道。
“哦,鳄鱼是怎么回事?”
詹金斯惊恐地转过头,望向棕色的水面。
接着,西蒙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包括他与两名阿拉伯人的冲突,刚刚讲完,船夫过来请他们到船尾吃饭。
方特希尔从背包里掏出一件干净的衬衫,套在穆斯塔法的头上,用绳子绑在腰间,卷起袖子。
这件衬衫有点大,看起来像是一个袍子。
当他们都坐在船尾的木架上,用手抓饭吃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只是穆斯塔法吃起饭来更急切一点。
当然,西蒙还是让大家密切监视岸上情况,詹金斯手里始终握着柯尔特手枪。
“我们应该谈谈,”艾哈迈德在用餐结束时说。
三个人走到船头,留下男孩和船夫洗餐具。
艾哈迈德焦急地沿着主街往下看,然后沿着河边小路扫视了一遍,“除了强盗的危险,我们不能留住逃跑的奴隶”,他略带怒气地低声说,“对苏丹人来说,这就是抢劫,他们不喜欢。
他的主人是马赫迪的追随者,如果被那个人发现,我们就会遇到大麻烦。”
“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他?”
詹金斯问,“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忠诚的人,不是吗?”
艾哈迈德摇了摇头,“是难找到。
但现在他在我们这里的消息,整个村子会知道,整个沙漠也都会知道。
我们把衬衫给他,把他留在这里。”
“哦,天哪,”詹金斯说,“不是那件衬衫,老伙计,如果你不介意,这是你最好的。
我有一件旧的,可以送他。
但是.......”他回头看了看,男孩正和船夫愉快地聊天,“把他留在这似乎不妥,我们看他时,他正盯着我们看。”
“如果买主真地找过来,那我就得拿孩子背上的伤痂来好好说道说道。”
詹金斯和艾哈迈德彼此交换一下担忧的目光,“西蒙,这明智吗?”
埃及人问,“如果我们遇到他的主人,就会有麻烦,可能不得不打一架,我想会非常碍事的。”
方特希尔笑了,但没什么幽默感,“如果我们真遇到那个混蛋,我会克制住自己,尽量不杀他,然后从他手里买下那个男孩”,他弯下身子向前看了看,“奴隶制在苏丹很普遍,是这个该死的国家最大宗的贸易,我们和奴隶一起旅行完全正常。
他会说英语,又在喀土穆长大,简首是天助我也。
我敢打赌,即使喀土穆被围,他也能找到进城的路。
至于打架时碍事,上帝啊,你应该看到他是怎么对付鳄鱼的。
如果算是我救了他的命,他也肯定会救我的命。
我想他会愿意跟我们一起的。
那么,艾哈迈德,让你找的骆驼呢?”
艾哈迈德耸了耸肩,但脸色变得轻松起来,“这倒是个好消息。
我买到三匹骑乘骆驼和两匹驮行李的骆驼。
至于你的骆驼,西蒙,它很漂亮” ,他们对这老梗咧嘴一笑,“我买的很合算。
更重要的是,我听说到有一条穿过沙漠到阿卜杜姆的小路,就从下游一英里处开始,我们不能错过。
这个男孩会走路吗?”
“啊,他跟威尔士牧羊犬一样轻,”詹金斯说,“可以坐在行李上。”
第二天一大早,小队出发了,很快就把尼罗河抛在身后。
穆斯塔法穿着新衬衫,骄傲地走在前面,头上系着一块旧麻布。
西蒙骑在骆驼上,当然,它和别的骆驼一样丑,当血红的太阳在东方升起时,他眯起眼睛,不知道他的未婚妻爱丽丝是否己经原谅他了。